前一頁
回目錄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与《波動》
食指的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16与趙振開的小說《波動》17,不但与“文革中”的公開發表的文學大相徑庭,即使与五六十年代公開發表的作品相比,也具有迥然不同的特點。這標志著年輕一代不但在精神上從“烏托邦神話”中覺醒,而且嘗試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感性体驗与理性思考,從而走出政治權力者制造的夢魘,回歸到個体的真實体驗,也因此它們具有一种滌除了政治權力話語之后的真率与清新。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与作者的另一首詩《相信未來》一起在知青中廣為流傳。作為上山下鄉隊伍中的一員,在即將离開故鄉北京的一剎那,作者的心靈突然受到強烈的触動,這种触動包括對故鄉、母親、文明的眷戀,也許還包括對不可知的未來的恐懼。“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在“一片手的波浪翻動”与“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中”,詩人突然感到:"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我雙眼吃惊地望著窗外,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只風箏,風箏的線繩就在媽媽的手中。"
在當時的官方政治話語里“上山下鄉”被解釋為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改天換地、大有作為的神話,從而掩蓋了當事人的真實感受,食指這樣的詩卻以真率朴素的態度,將個体的真實而獨特的經驗彰顯出來。他具有天生的詩人的敏感气質,表現在這首詩中就是敏銳地抓住個体的“我”心靈中的几個幻覺意象,并把它們自然而集中地組合起來,這在1949年以后的大陸文學中是很罕見的。幻覺中“劇烈地抖動”的“北京車站”,作為“我”的心靈的外化,強烈地表現了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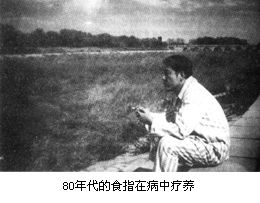 的感情震動之巨,表現了那种“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的茫然与無助。另一個“幻覺蒙太奇”也很精采,“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對“幻覺”的出色表現,在文革中年輕一代的藝術探索中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手段,表現出他們對政治權力話語的輕蔑与反叛。只是与西方現代主義起源于對“人”的深刻怀疑不同,中國年輕一代的藝術探索從一開始就以對人的肯定作為其目的与出發點,“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所表現的正是文學中源遠流長的對母愛的眷戀,在這种普通而強烈的人性面前,政治權力者們制造的所有神話都褪去了絢爛的光彩,顯得蒼白無力,而隱藏在其背后的現實的黑暗、悲哀与人性永恒的喟歎赤裸裸地表露出來。
的感情震動之巨,表現了那种“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的茫然与無助。另一個“幻覺蒙太奇”也很精采,“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對“幻覺”的出色表現,在文革中年輕一代的藝術探索中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手段,表現出他們對政治權力話語的輕蔑与反叛。只是与西方現代主義起源于對“人”的深刻怀疑不同,中國年輕一代的藝術探索從一開始就以對人的肯定作為其目的与出發點,“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所表現的正是文學中源遠流長的對母愛的眷戀,在這种普通而強烈的人性面前,政治權力者們制造的所有神話都褪去了絢爛的光彩,顯得蒼白無力,而隱藏在其背后的現實的黑暗、悲哀与人性永恒的喟歎赤裸裸地表露出來。
趙振開的小說《波動》被稱為“從黑暗与血污中升起的星光”,其中也有類似的對幻覺的描寫。在女主人公蕭凌的意識中,母親慘死的場面作為一种“創傷性經歷”不斷地強烈地回复到她的幻覺中:
“皮帶呼嘯著,銅環在空中閃來閃去。突然,媽媽沖出重圍,向陽台跑去,她敏捷地翻到欄杆外面。‘反正一死,誰要過來,我就跳!’一切都靜止了。天那么藍,白云紋絲不動,陽光撫摸著媽媽額角上的傷口。
‘ 媽媽——’我大叫一聲。
‘ 凌凌——’媽媽的眼睛轉向我,聲音那么平靜。媽媽。我。媽媽。眼睛。血珠。白云。天空……
娃娃臉似乎清醒過來,他用皮帶捅捅帽檐,向前邁了一步。‘跳呀,跳呀!’我扑上去,跪在地上緊緊抱住他的腿,用苦苦哀求的目光望著他。他低下頭猶豫著,嘴唇微微張開,露出亮閃閃的牙齒。他咽了口唾沫用力把我推開。
“媽媽——”白云和天空陡地翻轉過來。“
很難設想,如果不是這种蒙太奇式的幻覺描寫,食指詩歌与趙振開小說中的強烈情感如何表現出來。在當時的流行的藝術模式中,個人的愛憎感情必須以階級標准來判斷,“小我”的感情必須服從“大我”的理想,在這种話語模式中,個人的真正的感情必須按階級的標准來過濾与消解,其任何流露如果最終不歸結為對革命理想的襯托都有可能被認為是可疑甚至是反動的。(即使在當時知青的地下文學中,這种話語模式也頗有市場,其典型例子如同樣表現年輕一代中思想沖突的長詩《決裂。前進》。)在這一背景下反觀食指与趙振開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其精神上的覺醒与藝術上的探索的同步性。這种藝術探索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對現實進行祛魅除幻,其目的正如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所說的,是“為了恢复對生活的感受,為了感受到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18就此看來食指与趙振開對個人主觀感受的表現,無疑是沖破文革中虛假的權威話語對個人的真實生活經驗的遮蔽的有力手段,在這种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的藝術中,蒙在時代表面的燦爛輝煌的神話面紗才被撕得粉碎,顯示出現實“黑暗与血污”的真相。在此之后,人性的覺醒才有可能隨著個人的覺醒進入人們的腦海与視野之中。
事實上,食指詩歌与趙振開小說中充滿了個人象征与個人意象。上舉的幻覺意象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而《波動》中的個人象征与個人意象還要丰富,“書中那座城市充滿了純粹的錯覺、塤坏的偶像、邪惡、暴力、种种荒謬還有孤獨。”如楊訊出場時的敘述:“車站小廣場飄著一股甜膩膩的霉爛味。……一路上,沒有月亮,沒有燈光,只是在路溝邊草叢那窄窄的葉片上,反射著一點一點不知打那儿來的微光。”這种充滿了個人情緒的意象為全書定下了壓抑的基調,有一种整体的效果。又如蕭凌的意識活動,其中有些意象特別具有尖銳的刺激力:
“我和黑夜面對著面。
空虛、縹緲、漫無目的,這是我加給夜的感覺,還是夜加給我的感覺?真分不清楚,哪儿是我,哪儿是夜,似乎這些都渾然一体了。“"天空變得那樣黯淡,那樣狹小,象一塊被海鳥銜到高處的肮髒的破布。"
類似的例子舉不胜舉。在看慣了當時充斥在公開發表的文學中的那种虛假、枯燥、干癟与程式化的共同象征之后,再看這些個人性的象征与意象,雖然傳達的一种壓抑的情緒,但還是讓人感受到生人的清新气息。
在個人的主体性回复之后,政治權力話語對現實的權威解釋模式必然發生動搖,代之而起的是獨特的個人在与其血肉相關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對現實与未來的思考。這些充滿個人性的思考必然會激起更多的尖銳的矛盾与沖突,從而形成一個“多音齊鳴”的世界。就這一點而言,《波動》無疑得風气之先。小說的采用了复調敘述的方式,主要的敘述者不但有主人公楊訊与蕭凌,還有充滿矛盾的地方領導林東平及其女儿,徹底的虛無主義者、充滿了原始獸性的流浪漢白華等等。這些敘述者的不同視角展現出那個特定年代的現實的方方面面,以及不同經歷与地位的人們沖突而矛盾的內心世界,從而展示了一幅多角度、多側面的時代圖景。以相戀的主人公楊訊与蕭凌而言,同是時代的反叛者,他們的內心世界卻有很大的差异与沖突。對這一點的表現是小說最成功的地方,因為這兩個主人公代表了覺醒中的知青一代中的兩种典型心態,他們的個性互相沖突而又互相襯托。蕭凌几乎經受了人世間最為慘烈的苦難,父母慘死以及被前男友拋棄的創傷性經驗使她變得孤僻而封閉,趨于极端的怀疑主義,她不相信什么“終极的意義”,認為那只不過是“一种廉价的良心達到一种廉价的平衡的手段”. 她眼中看到的是現實的黑暗与血污,正如她所說:“這代人的夢太苦了,也太久了,總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會發現准有另一場惡夢在等著你。”与此相反,楊訊卻愿意設想“一個比較好的結局”,插隊時因農村大旱他領頭反對交公糧并因之被逮捕的經歷,也沒有使他擺脫自己的理想主義。然而相對來說,由于其高干家庭出身,他沒有更直接地面對現實的血淋淋的殘酷,他的理想主義未免顯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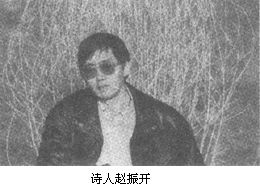 些淺薄,正如蕭凌一針見血地指出的:“……你們總是相信結局……,因為在每個路口都站著這樣或那樣的保護人,”“你們畢竟不用付出一切,用不著挨餓受凍,用不著遭受歧視与侮辱,用不著為了几句話把命送掉……”,由于這种淺薄,他得知蕭凌有私生女時,不能体會她的難以言說的痛楚而殘酷地与她分手。但在另一方面,這兩個人物能走到一起,就有其共同之處,這就是對人性的執著。他們雖然各趨一端,但又互相補充。即使极端絕望的蕭凌也企圖在充滿了“粗暴”、“狂野”与“殘忍”的環境中保住人性中的一點“优雅”与“詩意”,而永遠不可能与殘酷粗暴的現實協調。這一點“优雅”与“詩意”,就是在時代的黑暗中一點人性的“星光”。“星光”這一意象,在小說中多次出現,正如楊健所指出的“星光是這個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沒有溫暖陽光的時候,這冷冷的光明就顯得极其寶貴。這星光就是深藏在蕭凌等人心底的未曾泯滅的人的良知。這星光是對要不變為獸或畜生,而保留的一點對人性的執著。”19可以說,這一點對人性的執著,是年輕一代精神上覺醒的契机与藝術探索的動力,它也為文革后中國文學的复蘇作了預告。
些淺薄,正如蕭凌一針見血地指出的:“……你們總是相信結局……,因為在每個路口都站著這樣或那樣的保護人,”“你們畢竟不用付出一切,用不著挨餓受凍,用不著遭受歧視与侮辱,用不著為了几句話把命送掉……”,由于這种淺薄,他得知蕭凌有私生女時,不能体會她的難以言說的痛楚而殘酷地与她分手。但在另一方面,這兩個人物能走到一起,就有其共同之處,這就是對人性的執著。他們雖然各趨一端,但又互相補充。即使极端絕望的蕭凌也企圖在充滿了“粗暴”、“狂野”与“殘忍”的環境中保住人性中的一點“优雅”与“詩意”,而永遠不可能与殘酷粗暴的現實協調。這一點“优雅”与“詩意”,就是在時代的黑暗中一點人性的“星光”。“星光”這一意象,在小說中多次出現,正如楊健所指出的“星光是這個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沒有溫暖陽光的時候,這冷冷的光明就顯得极其寶貴。這星光就是深藏在蕭凌等人心底的未曾泯滅的人的良知。這星光是對要不變為獸或畜生,而保留的一點對人性的執著。”19可以說,這一點對人性的執著,是年輕一代精神上覺醒的契机与藝術探索的動力,它也為文革后中國文學的复蘇作了預告。
注釋:1 引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收入謝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 頁。
2 文革后期文學(藝)類雜志的复(創)刊,最早的當屬《北京新文藝》(1971.12 ),這也許是一個率先發出的信息。但在全國范圍來看,總体上呈現出“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1972年1 月,先有《廣西文藝》、《廣東文藝》、《革命文藝》(內蒙)复刊,隨后吉、魯、黔、川、湘等省市的文藝刊物也陸續复刊,到次年夏季,全國除上海(影響重大的文藝叢刊《朝霞》也于是年5 月在上海創刊,但它直接受“四人幫”控制)、天津、江蘇、浙江等省市外的大部分省市都有由當地文聯或作協主辦的刊物复(創)刊,而滬、津、江、浙等地,也已有地市一級文藝刊物刊行。參見《新中國文學詞典。附錄。文學刊物刊名變更情況一覽》,第1310-1330 頁,潘旭瀾主編,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3 《金光大道》共有四卷。第一、二兩卷分別于1972年8 月和1974年5 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4年夏由京華出版社重版,并一次出齊四卷。
4 《虹南作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51973 年7 月28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審查湘劇舞台藝術片《園丁之歌》時,對影片橫加指責,扣以“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的罪名,一年后,該片在全國范圍遭到批判。
6 根本任務論是在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上正式提出的,即將塑造工農兵英雄人物規定為“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參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收入謝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 頁。
71968 年5 月,于會泳在《文匯報》發表《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一文,依江青指示歸納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來;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來;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來”. 后來經姚文元改定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這一原則被廣泛運用于電影鏡頭的運用、舞台調度、情節安排等各個方面,既是創作原則又是批評標准。這個原則還演繹出三陪襯、多側面、多浪頭、多回合、多波瀾、多層次和高起點等一系列“三字經”創作模式,將人物和情節簡化為固定公式。
8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 頁。
9 同上書,第87頁。
10張清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頁。
11《緣緣堂續筆》据《丰子愷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12《丰子愷散文全編》,第662 頁。本教材所引用的丰子愷語均依据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13《半棵樹》初刊于《詩刊》1982年2 月號。
14本節引文均引自《對于人生和詩的點滴回顧和斷想》,見牛漢《學詩手記》,三聯書店1986年版。
15本詩初次發表于李方編《穆旦詩全集》,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本節即依据此版本。
16《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原是地下手抄作品初次發表于《今天》文學雙月刊第四期,后被編入多种選本,本教材依据的是林莽、劉福春編《詩探索金庫。食指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7《波動》原系地下手抄作品,出次發表在《今天》文學雙月刊四、五、六期連載,用筆名“艾珊”. 首次公開發表于《長江》1981年第1 期。本教材依据的是小說集《歸來的陌生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18《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頁。
19引自同注8 書,第168 頁。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