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頁
回目錄
《半棵樹》与《神的變形》
詩人牛漢1955年由于胡風事件的牽連,遭到兩年的拘捕囚禁,釋放后也失去了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作品的權利。“文革”開始后,他理所當然地被關進“牛棚”接受批斗、從事強制性的勞動。但這些并沒有使他失去創作的欲望,相反,逆境生涯反而激發起了他更加強烈的生命意識。牛漢40年代的詩歌充滿了一种反抗的火力,而寫于1970年到1976年的几十首詩歌,如名詩《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半棵樹》、《巨大的根塊》等,則大部分屬于他所謂的“情境詩”,這些詩歌相對他早期的詩來說語調比較平靜,但在內里則仍充滿了堅韌的反抗精神。這些詩歌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識,他借助不同的意象,表達了陷于逆境的生命的不屈地抗爭与堅韌地生存的精神,也高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的抗爭与現實戰斗的傳統。
以《半棵樹》13為例,處于全書中心地位的是一個极端變形的意象:“半棵樹”. 詩人寫到:"真的,我看見過半棵樹在一個荒涼的山丘上""象一個人為了避開迎面的風暴側著身子挺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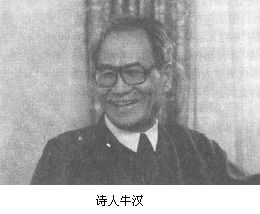
牛漢早期學過繪畫,所以他對視覺意象特別敏感,那极端怪异的“半棵樹”的形象想必是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心靈,詩人聯想:“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電/ 從樹尖到樹根/ 齊楂楂劈掉了半邊”,這必然使他對自己的身世与處境產生強烈的触動,在歷次運動中的知識分子,不是也被政治權力的雷電,“齊楂楂劈掉了半邊”嗎?可是:"春天來到的時候半棵樹仍然直直地挺立著長滿了青青的枝葉""半棵樹還是一棵樹那樣高還是一棵樹那樣偉岸"
在這里,半棵樹的象征意味就更加明顯了,它象征著不屈的生命,象征著知識分子不屈的抗爭与戰斗的傳統,這個意象很有些“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味道,但那個恐怖的時代卻使得詩人產生了不祥的預感,在抒寫了一种堅韌頑強的意志后,他在詩的結尾又寫道:“人們說/ 雷電還要來劈它/ 因為它還那么直那么高/ 雷電從遠遠的天邊就盯住了它”. 牛漢一直認為:“任何一首真正的詩,都是從生活情境中孕育出來的,离開產生詩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無法理解詩的。”所以他說:“‘文革’期間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寫的那些詩,如果把它們從生活情境剝离開來,把它們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詩,就很難理解那些詩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針對性,很難理解到產生那些情緒的生活境遇。”他在這段時間寫的這類詩,多半吟誦被侮辱与被損害的生命,像被伐倒的楓樹、不斷地被斫伐的灌木、囚籠里因為反抗甚至抓破了指爪的華南虎、在地下的黑暗中默默生長的根塊等等,但這些意象中還是以“半棵樹”的意象最為引人注目,那种被斫去了一半身軀卻依然堅韌不拔、生命不息的意象,鮮明地体現了文革中正直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形象,而詩歌最后一段的突然轉折,則又顯示出一种惊人的清醒。《半棵樹》代表了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如七月派作家群)在文革中的“潛在寫作”仍然帶有反抗的英雄的風格,雖則“都不可避免地帶著悲凄的理想主義的基調。”14
40年代中國最优秀的青年詩人穆旦在1949年后的遭遇也很坎坷,1954年,他因為抗戰中參加遠征軍的經歷被查成為“肅反對象”,1958年底,被逐出講堂,強迫在南開大學圖書館“接受机關管制”,監督勞動。此后才華橫溢的一代詩人与翻譯家每日被迫從事整理圖書、抄錄索引以至打掃廁所之類的繁重工作,“文革”發生后他的處境更加艱難。但就是在二十余年的困憊處境中,他堅持翻譯了《丘特切夫詩選》、《唐璜》、《拜倫抒情詩選》、《西方當代詩選》、《歐根。奧涅金》等皇皇巨著,顯示出中國最优秀的知識分子在逆境中仍然堅守自己的精神崗位、為文化建設努力的优良傳統,這与几十年文化傳統不斷被破坏的外部情境相對比,更顯其精神之偉大堅強。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被迫中斷寫作近2 0年后,他在去世前的一年多時間里(1975-1976)重新開始詩歌寫作,不但一點不見詩藝的衰退,而且由于几十年坎坷經歷的浸泡,顯得更加意蘊深厚。穆旦去世前給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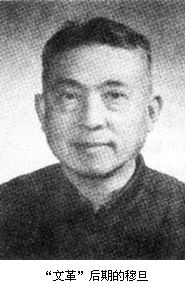 留下的几十首詩,現在看來,無疑屬于文革中的潛在寫作中最优秀的詩歌之列。這些詩歌仍然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詩藝,在層層轉折中表達著對個人身世的慨歎、對時代的烏托邦理想的審視与反諷,基調是冷峻甚至無奈的,有些詩篇如《停電以后》、《冬》等仍顯示了一种在黑暗之中堅持崗位的精神--不過更多的是表達几十年坎坷之后所獲得的苦澀的智慧,像詩人自己說的:在走到幻想的盡頭、過去的所有歡喜都像落葉一樣“枯黃地堆積在內心”的時候,“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 它的碧綠是對我的無情的嘲弄,/我咒詛它每一片綠葉的生長”。我們所要討論的《神的變形》無疑也屬于這种以苦汁為營養的智慧之列。
留下的几十首詩,現在看來,無疑屬于文革中的潛在寫作中最优秀的詩歌之列。這些詩歌仍然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詩藝,在層層轉折中表達著對個人身世的慨歎、對時代的烏托邦理想的審視与反諷,基調是冷峻甚至無奈的,有些詩篇如《停電以后》、《冬》等仍顯示了一种在黑暗之中堅持崗位的精神--不過更多的是表達几十年坎坷之后所獲得的苦澀的智慧,像詩人自己說的:在走到幻想的盡頭、過去的所有歡喜都像落葉一樣“枯黃地堆積在內心”的時候,“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 它的碧綠是對我的無情的嘲弄,/我咒詛它每一片綠葉的生長”。我們所要討論的《神的變形》無疑也屬于這种以苦汁為營養的智慧之列。
《神的變形》15是一出小小的詩劇,可是其內涵卻包蘊了歷史上的各种權力運作的机密,自然,其直接的針對性更讓人聯想起“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的社會現實。詩劇有四個人物:神、魔、權力、人。一開始,曾經“浩浩蕩蕩”、“掌握歷史的方向”的神發現:“可是如今,我的体系像有了病”. 權力接著登場,它毫不猶豫地宣稱:“我是病因。你對我的無限要求/ 就使你的全身生出無限的腐銹。/ ……而對你的任性,人心日漸變冷,在那心窩里有了另一個要求。”這另一個要求就是魔,魔代表著反抗,神被無限的權力所腐蝕,魔從他那里奪來了“正義、誠實,公正和熱血”作為自己的營養,魔在人心里滋長著,呼喚著“決斗”,由它來繼承歷史的方向。這時候人登場了,人處于“神”和“魔”爭斗的中間,它們都呼喚著人起來幫助它們打倒對方,可是人已經厭惡了神,也不相信魔,他們已經看清了真理,該首先擊敗的是“無限的權力”,他們多少個世紀被卷進“神魔之爭”,然而“打倒一陣,歡呼一陣,失望無窮,/ 總是絕對的權力得到了胜利!、神和魔都要絕對地統治世界,/ 而且都會把自己裝扮得美麗!”人感歎自己是多么容易受騙,然而他們現在已經“看到一個真理。”如果詩劇在這儿結束,在“文革”那個年代里,它仍不失為振聾發聵之作,可是穆旦不是廉价的樂觀主義者,他讓人在魔鬼的誘騙下再一次上當,人再一次落入了歷史的循環,起來反抗,滿心以為“誰推翻了神誰就進入了天堂”,這時候權力冷冷地發話:"而我,不見的幽靈,躲在他身后,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寶座,我有种种幻術越過他的誓言,以我的腐蝕劑伸入各個角落;不管原來是多么美麗的形象,最后……人已多次体會了那苦果。"
這是一种貌似冰冷的智慧,然而仔細辨析,詩人在做出這樣的判斷后內心充溢的仍然是深深的苦澀。通過這四個人物戲劇性的沖突与聯系,它展示了一個人類歷史悲戲劇的寓言,同時也是一個酸楚的預言。
穆旦在40年代就受奧登等人的影響,富于理性的思考、以思想入詩是他的詩歌一貫的特色,這首詩也不例外,可是它的特點在于并不是直接的思想演繹,而是把思想戲劇化,在戲劇的結构中展示思想的全過程。《神的變形》至少有三個層次的轉折:魔的反抗是一個轉折,人的覺醒是第二層轉折,而人最后仍舊落入魔的圈套是第三層轉折,權力的冷冷的插話,使得這三個轉折构成一個圓圈,象征著人類歷史可悲的循環,思想的層層轉折、深入、循環的過程,通過戲劇化的結构表現得非常生動,從而也就有了一种內在的形象性。它也不是沒有情感,只是情感深深地潛隱在思想的底層,決不作過剩的流溢,卻也因此獲得一种深度与力度,使得有能力触及到這种情感的人獲得一种震憾。《神的變形》同時有一個潛在的神話結构,就是從彌爾頓以至浪漫主義思潮以來的“神魔爭斗”的神話原型,在這個原型中,“魔”是代表爭取自由的反抗者的形象出現,穆旦運用這個原型卻對之作了反諷式的處理,這不再是近代式的朴素的“壓迫——反抗”的戲劇,他發現“反抗者”也可以成為壓迫者,而人的歷史仍是循環的怪圈。這其實也展示了一种現代主体的分裂:無論是神、魔還是人自身的理智与感情,其實都是這個現代主体的不同側面,“神的變形”這個循環實際上說明了現代主体在權力的運作秩序之中的分裂、變形、軟弱与無力,自然這里也有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苦澀的智慧,處于文革的逆境中的穆旦仍然保留了濃重的現代意識。
“七月”派与“中國新詩派”詩人在4 0年代分別被批評家稱為“現代的堂吉訶德与哈姆雷特”,通過以上解讀,我們可以發現在文革中,他們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獨特的气質:一個是憤怒的反抗,一個是猶疑的智慧,只是在這時“堂吉訶德”已經飽經挫折,其理想主義已經不無酸辛,而“哈姆雷特”以他的智慧更加發現了時代的可悲与苦楚。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