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頁
回目錄
《桂林山水歌》与《長江三日》
對于60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來說,雖然剛剛經過了嚴峻的大饑荒的災難,但其建构的時代共名已經不可動搖地被确立了主導地位。文學界進入了一個宏大敘事的“抒情時期”,“現實實際上是指對現實的一种判斷。對現實的描寫与熱情本身意味著一种抒情”6.這种抒情性在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中是以貌似客觀的面目出現的,即通過對客觀景物的描寫來表現,古老的借景抒情手法所抒的不再是個人的感触,而是借自然界的秀美与崇高來隱喻時代的美好与崇高,傳統的藝術技巧也帶上了新的意識形態色彩。賀敬之《桂林山水歌》与劉白羽的《長江三日》7 是這种現象的典型代表。
這兩個作品都成功于對景物的描寫与刻畫,文体上帶有“賦”的特征。《桂林山水歌》開始對景色的概括描寫:“云中的神啊,霧中的仙,/ 神姿仙態桂林的山!//情一樣深呵,夢一樣美,/ 如情似夢漓江的水!……”在今天讀來,這些詩句還是具有較好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劉白羽也有描寫景物的才能,《長江三日》對三峽景物的描寫,不論是瞿塘峽的險峻、巫峽的秀美還是西陵峽的凶惡,都有出色的描繪。正如漢賦浸透了漢帝國剛建立時的精神气韻一樣,這兩個作品也顯示了對國家政權的膜拜和信念,甚至比漢賦表現得更為直接。“桂林山水”在賀敬之的筆下成了戰士豪情的襯托:“桂林山水入胸襟,/此景此情戰士的心……” 山水之美在古典文學中常常引起一种空靈而惆悵的感喟,山水之永恒常常襯托出人生的短暫,可是時代精神的熏染使得賀敬之有能力把山水之美轉換成戰士的豪情,而且一點不帶
 惆悵与感傷的气息,這是因為他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分享了時代的本質,小我在大我之中獲得了擴張与永恒,所以不再會有人生短暫的感覺。這种豪情使他甚至要到“七星岩去赴神仙會,/ 招呼劉三姐呵打從天上會//……三姐的山歌有十万八千籮,/ 戰士呵,指點江山唱祖國……”天上地下,海北山南,都在這個戰士詩人“指點江山”的范圍之內,然而指點江山只是“起興”,目的是要“唱祖國”. 他展眼望去“紅旗万梭織錦繡,/ 海北天南一望收!”終于唱出了他的頌歌的最強音,時代的豪情接通了他的詩情,使他“意滿怀呵才滿胸”,“汗雨揮洒彩筆畫──/ 桂林山水──遍天下”,完成了對山水描繪向對時代頌歌的轉化。劉白羽同樣通過描寫來抒情,但他的抒情有一個過程,不同于賀敬之的直接抒情。長江“開闊──狹窄──開闊”的旅程,使他產生“戰斗──航進──穿過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于是他的旅程也就帶上了意識形態的象征色彩:
惆悵与感傷的气息,這是因為他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分享了時代的本質,小我在大我之中獲得了擴張与永恒,所以不再會有人生短暫的感覺。這种豪情使他甚至要到“七星岩去赴神仙會,/ 招呼劉三姐呵打從天上會//……三姐的山歌有十万八千籮,/ 戰士呵,指點江山唱祖國……”天上地下,海北山南,都在這個戰士詩人“指點江山”的范圍之內,然而指點江山只是“起興”,目的是要“唱祖國”. 他展眼望去“紅旗万梭織錦繡,/ 海北天南一望收!”終于唱出了他的頌歌的最強音,時代的豪情接通了他的詩情,使他“意滿怀呵才滿胸”,“汗雨揮洒彩筆畫──/ 桂林山水──遍天下”,完成了對山水描繪向對時代頌歌的轉化。劉白羽同樣通過描寫來抒情,但他的抒情有一個過程,不同于賀敬之的直接抒情。長江“開闊──狹窄──開闊”的旅程,使他產生“戰斗──航進──穿過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于是他的旅程也就帶上了意識形態的象征色彩:
“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這時一种庄嚴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在我的心靈,我覺得這是我所經歷的大時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現在這奔騰的長江之上。是的,我們的全部生活不就是這樣戰斗、航行、穿過黑夜走向黎明的嗎?……我們的哲學是革命的哲學,我們的詩歌是戰斗的詩歌,正因為這樣──我們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話說的好极了:“前進吧!──這是多么好啊!這才是生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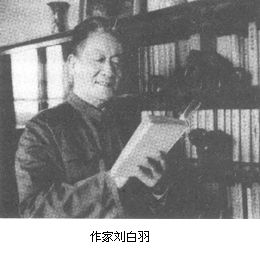 《長江三日》寫于大躍進失敗之后,作者不斷強調戰胜阻礙、向前航行的意義。文章中不斷出現這類象征性的意象,一會儿是險峻的峽谷中“一注陽光象閃電樣落在左邊峭壁上”,一會儿是“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來這青灘的聲勢十分嚇人,但人從洶涌浪濤中掌握了一條前進途徑,也就戰胜大自然了”,等等。這篇文章的最后面對冷戰時代的“世界”,它歌頌“今天我們整個大地所吐露出來的那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這社會主義的呼吸,正是全世界上,不管在亞洲還是歐洲,在美洲還是在非洲,一切先驅者的血液,凝聚起來,而放射出來的最自由最強大的光輝。”這种聲音已經是直接代時代抒情了。這兩部作品的抒情主体無例外都是一個“我”,但這個“我”最后都不是個人,而是“歷史”、“現實”、“時代”的化身,當個人毫無保留地參与到時代共名的宣傳之中,個人事實上已經不再是個人了,所以這個“我”的抒情才能有那么大的豪情与气魄。
《長江三日》寫于大躍進失敗之后,作者不斷強調戰胜阻礙、向前航行的意義。文章中不斷出現這類象征性的意象,一會儿是險峻的峽谷中“一注陽光象閃電樣落在左邊峭壁上”,一會儿是“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來這青灘的聲勢十分嚇人,但人從洶涌浪濤中掌握了一條前進途徑,也就戰胜大自然了”,等等。這篇文章的最后面對冷戰時代的“世界”,它歌頌“今天我們整個大地所吐露出來的那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這社會主義的呼吸,正是全世界上,不管在亞洲還是歐洲,在美洲還是在非洲,一切先驅者的血液,凝聚起來,而放射出來的最自由最強大的光輝。”這种聲音已經是直接代時代抒情了。這兩部作品的抒情主体無例外都是一個“我”,但這個“我”最后都不是個人,而是“歷史”、“現實”、“時代”的化身,當個人毫無保留地參与到時代共名的宣傳之中,個人事實上已經不再是個人了,所以這個“我”的抒情才能有那么大的豪情与气魄。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