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頁
回目錄
《陶淵明寫》
陳翔鶴是從“五四”時期就開始創作的老作家,也是當時最堅韌的文學社團“淺草社”、“沉鐘社”的主要成員,他1949年以前的創作多取材自現實生活,帶有濃重的感傷色彩,一方面感覺覺醒之后無路可走,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屈服。1949年以后,他長期擔任編輯工作,很少有創作發表,1961、1962兩年卻得風气之先,連續發表《陶淵明寫 》与《廣陵散》兩篇歷史小說,引發了歷史小說創作的一個小高潮。
在60年代,選取陶淵明、嵇康這樣的歷史人物作為小說的主人公,本身就顯示出一种与“時代共名”保持距离的態度。無論是陶淵明還是嵇康,在歷史上都是很有個性的人物,他們与各自所處身的時代的權力秩序,處處顯得格格不入。像這樣的人物,不論以其階級出身還是以其特立獨行的性格而言,都不可能成為60年代國家意志占据主導地位的時代主流所欣賞的時代英雄,而只可能成為爭議性的人物,對其人格与生活態度的欣賞,也只可能是個人性的,何況陳翔鶴在小說中并沒有刻意去迎合時代共名,將他們塑造為“反抗的英雄”,而是著重表現對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持不合作的精神立場的知識分子的無力之感。這樣的“無力”的知識分子形象,當然不符合時代的需要,但卻毫無疑問具有一种從個体心靈出發的真實性,也彰顯了一种真實的知識分子的生存樣態,這正是文學所應該表現的而時代共名企圖刻意抹殺的。
与傳統的觀點不同,陳翔鶴在《陶淵明寫 》中塑造的陶淵明形象,強調的不是達觀的生存態度,而是潛藏在這种達觀態度后面的感慨与“殷憂”. 小說中的陶淵明,自覺地与權力中心--不論是精神上的權力中心,還是現實的政治權力中心保持一种疏离關系,前者如他對廬山法會上慧遠和尚的“傲慢、淡漠而又裝腔作勢的態度”的否定,后者如他對慕名而來的聲威赫赫的刺史檀道濟的反感与厭惡。這兩种權威,在小說中都以一种諷刺的筆調寫出,例如廬山法會上的慧遠,“儼然是另一种達官貴人的派頭”,“只見他半閉著眼睛,雙手合十,一任香客們在他座前四禮八拜,臉上紋風不動,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真不知他是在睡覺呢還是在閉目養神。”一直到法會結束,“這時他才微微地動了一下眼皮,在鐘鼓齊鳴中,喃喃念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念畢這种神秘而又令人難懂的咒語之后,他甚么也沒有說,便下得座來起身入內了。對于那些匍匐在地面上的會眾,連正眼都不曾看一眼,更不用說和气地來同大家打個招呼了!”“這种毫不理會大家的態度,給陶淵明以一种大有‘我慢’之慨的印象。而這种‘我慢’,又正是慧遠本人對陶淵明所時常提起,認為是違反佛理的。”顯然,作者有意識地把慧遠塑造為自相矛盾、心口不一而且儼然真理在握的人物。進一步說,雖然他也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在行為上也可以不合世俗,但在根本上他并沒有完全擺脫世俗的習气,沒有自外于現實的權力結构,在根本的道理上,依然有“未達”之處,用陶淵明的話說就是:
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又算得個甚么!哪值得這樣敲鐘敲鼓地大惊小怪!佛家說超脫,道家說羽化,其實這些都是自己仍舊有解脫不了的東西。
表面上看,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复獨多慮”的生死觀与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僅僅是一种義理上的分歧,實際上,陶淵明貌似達觀的生死觀背后隱含著沉痛的精神經驗,那就是對整個道德淪喪、乾坤淆亂的時代的疏离与拒斥的關系。小說結尾將這种整体性的疏离直接通過寫《挽歌》与《自祭文》的情節表達出來,也為陶淵明的生死觀作了一個形象的解說: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不錯,死又算得個甚么!人死了,還不是与山阿草木同歸于朽。不想那個賭棍劉裕竟會當了皇帝,而能征慣戰的劉牢之反而被背叛朝廷的恒玄破棺戮尸。活在這爾虞我詐、你砍我殺的社會里,眼前的事情實在是無聊之极;一旦死去,歸之自然,真是沒有什么值得留戀的!
“寫《挽歌》”的情節是整篇小說的中心与高潮,通過這個情節,小說將陶淵明的精神境界從對個別對象的否定引申到對整個顛倒混亂的時代的否定,從而只能与之采取一种疏离与對立的關系。由此出發,可以理解陶淵明特立獨行的精神立場,這不僅表現在他對政治權威与精神權威的拒斥上,也表現在他對不能脫俗的朋友的批評上,如批評顏延之“一天到晚都在同什么廬陵王、豫章公這一些人搞在一起,侍宴啦,陪乘啦,應詔賦詩啦,俗務縈心,患得患失,哪還有什么詩情畫意?沒有詩情,又哪里來的好詩!”這也顯示出他不僅僅是在語言上与時代疏离,而且在生活上也有意識地躬行踐履,自覺地保持自己獨立的精神立場不受時代污染。
一個自覺地疏离于整個時代的人,即使是大勇者,恐怕也難以擺脫這种疏离引起的孤立之感。陳翔鶴塑造的陶淵明,在達觀之外,還帶上了傷感、苦悶与悲憤的色彩。例如小說中設計了一個陶淵明吟詠、欣賞阮籍的《詠怀》詩的情節:“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感物怀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這首詩流露出濃重的憂世傷生的色彩,而又孤立、苦悶,舉世滔滔而莫能与之交流,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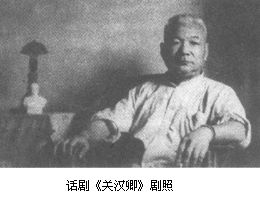 世嫉俗而又恐懼為世俗所覺、所害,构成詩里所說的“殷憂”。這种“殷憂”不僅是阮籍的,而且是小說主人公陶淵明的,也是小說家陳翔鶴自己的。不過小說中將陶潛塑造為一個遠离權力中心的隱士,恐懼的成分相對少一些,而更多孤立之感。但就作者來說,在小說中設計這樣一個細節,所流露出的就不僅僅是与時代主流疏离的孤立之感,而且明顯地顯示出一种不敢与別人交流這种“疏离”的隱憂,典型地体現出處身于國家權力构筑的“時代共名”的裹挾之下而又有自己獨特的精神立場以及不可磨滅的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苦悶心態。拒絕了時代主潮,而又無法阻擋這個時代主潮,由此必然產生一种無力之感,在達觀之外,難免有悲憤、苦悶、傷感。小說中陶淵明發出的“人生實難,死之如何”的感慨,一方面由于對時代主潮拒斥因而無所牽挂,針對的是整個時代,另一方面也針對自己的一生,針對的是顛倒錯亂的時代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的無力与無可奈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顛倒錯亂的時代良知与正義的無力与無可奈何),所以小說中潛伏著的感傷色彩在最后終于壓制不住而流露出來。當陶淵明念到《自祭文》中最后五句“……匪貴前譽,孰重后歌,人生實難,死之如何?嗚呼哀哉!”時:
世嫉俗而又恐懼為世俗所覺、所害,构成詩里所說的“殷憂”。這种“殷憂”不僅是阮籍的,而且是小說主人公陶淵明的,也是小說家陳翔鶴自己的。不過小說中將陶潛塑造為一個遠离權力中心的隱士,恐懼的成分相對少一些,而更多孤立之感。但就作者來說,在小說中設計這樣一個細節,所流露出的就不僅僅是与時代主流疏离的孤立之感,而且明顯地顯示出一种不敢与別人交流這种“疏离”的隱憂,典型地体現出處身于國家權力构筑的“時代共名”的裹挾之下而又有自己獨特的精神立場以及不可磨滅的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苦悶心態。拒絕了時代主潮,而又無法阻擋這個時代主潮,由此必然產生一种無力之感,在達觀之外,難免有悲憤、苦悶、傷感。小說中陶淵明發出的“人生實難,死之如何”的感慨,一方面由于對時代主潮拒斥因而無所牽挂,針對的是整個時代,另一方面也針對自己的一生,針對的是顛倒錯亂的時代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的無力与無可奈何(這實際上也是一個顛倒錯亂的時代良知与正義的無力与無可奈何),所以小說中潛伏著的感傷色彩在最后終于壓制不住而流露出來。當陶淵明念到《自祭文》中最后五句“……匪貴前譽,孰重后歌,人生實難,死之如何?嗚呼哀哉!”時:
一种濕漉漉、熱乎乎的東西,便不自覺地漫到了他的眼睛里。這時他引以為感慨的不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還有他整個艱難坎坷的一生。
這种感傷,絕不僅僅是歷史人物陶淵明的,作者陳翔鶴顯然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通過一种個人性的敘事立場,通過對歷史人物的追憶,作者陳翔鶴也由此間接地表露了一种個人性的面對時代的態度。
經歷各次運動的打擊,知識分子的心態不敢再作直接的表露,只能通過歷史故事曲折地表現。但這与“舊瓶裝新酒”式的肆意篡改史實的方法不同,它是在尊重史實、“知人心”的前提下的一种創作。黃秋耘對此有一個精彩的解說:“寫歷史小說,其竅門倒不在于征考文獻,搜集資料,言必有据;太拘泥于史實,有時反而會將古人寫得更死。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能夠以今人的目光,洞察古人的心靈,要能夠跟所描寫的對象‘神交’,用句雅一點的話說,也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罷。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体會到古人的情怀,揣摩到古人的心事,從而展示古人的風貌,讓古人有血有肉地再現在讀者面前”14. 也只有這樣,作者的現實寄托与歷史故事才能夠融為一体,作者的心聲与歷史人物的心聲也才能契合無間,作者的個性、愛恨褒貶也才能通過對歷史的重塑表現出來。就此來說,《陶淵明寫 》等小說遠遠超過了那些“借古頌今”、“以今例古”的戲劇,而為解讀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提供了很好的文本依据。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