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ؿ�
�@�@�@�@�@�@�@�@�m�d�D�������n�M�m�������~�n
�@�@�P�ܪ�����m�d�D�������n11�ɧU�ﰨ���ζH���yø�A���F�F�@���藍�����̪��ͩR�O�O�i�����V���O���D�C�@�a���q�L���Aij�װ����H���B�d�m�B�j�l���ζH�A���b�s�諸���W���O�����Ѧa�������@���ת���. �����M�����F������~§�A�o���M�O���F�ۥѪ��ͩR�O�A�O�H���O�B�ͦӫD�����A�ݱo����O�۵M�����G�����b�O�o�����H���ߡA�@�L���ɤ��ۡF��ɬ���X���o�����H�H�N�ۭ�A�}�����z���A�G�ӻ{�������O�i�����H���A�O�R�����ƨ��A�O�O�O�����������X��. ����M�A�����ζH�H���F�@�̦ۤv�藍�����̪��ۥѪ��ͩR�Ҭɪ��l�D�C
�@�@�峹������ӳ��u�嫬�a��E�X�����ͩR���O�O�H��ۥѹҬɪ��V�����ĦX�C�@�ӳ��u�O�@��1970�~�b�@�ӹA�������A�Ш|�ɧԨ����F�믫�������A�b�V�]�m�������a�W�a���g�b�����u�A���H�۰����b���B�_��B���D�M�ݮ��A�ڭ̪��߱��ܱo�}�ԡB�ήi�B���������A�����y�_�K�K�P���ۥѪ��ˤ��M�r���ۤv�R�B����O�A�O���h�ֵκZ�ڡI�������g�b�O�H�����P���Ūn�X��A�ͩR���j�O�R�ʧܩڵ۳��t�C�I���a�ԡA�b���������Ҥ��ϤH���Ũ�ۥѪ��ּ�--�F�ѤF�o�h�t�q�A�N�����z�ѧ@�̦�H�p�������_���C�b�t�@�ӳ��u���A�@�̶i�@�B�i�ܤF�o���ͩR�O���R�ʹF����P�ɰs�������g�þĵo���ҬɡA�ͩR����y�b�۵M���@���U�a����A�Ҧ����~�ɪ����̳�����b���������C�o�O�@�̦b�L��ɫB�U���d�D�����W�Ҩ��쪺�̧��諸���s�b�]�����G
�@�@���������b�Ҧ��s�����������Q���o�I�ӤF�A�n�a��A�Q�ɫB�����@�⥴�ۡA�Q�C�I����p���~�ۡA�Q��i�j�a�������u���{�q�E�ĵۡA���A�o���w�������F�q�L�ƨ��f�B�s�Y�F�X�ӡA�s�x�b�m���a�b�o�쳥�W�E�F�A�p�s�צ��j�s�A�j�s�b�B�ʤ��X�i�A�����@���٥s�B�ɶáB�ֳt���ʪ����ΨR�W�����I�������Z�A�e�I�Z���A���Y���o�A�O�v�ɭP�I�K�K
�@�@�������������n�b�j�a���X�����I�A�d�[�a�l���R��B�s�ۦb�������Ŷ��I���B���q�A�E�X�@�������W�h�����u�A����B������ѫB�I�A�M�p�n�B�n��´���a�߰ʾz���j�R�x�C�K�K��
�@�@�o�O�v�ɭP���O���b�y�J�O�@���o�Z�h�֪��ͩR�ҬɡA�]�O�@���짻���諸�R���������A�ϱo�ԨƤH���o�h�B�o���B�o�b���A�b�L���������쪺�N���ר����Τ��ɡ��A�]���b�H�ͪ������L���o�a����F�ͩR�ɯu�����R�����P�C
�@�@�P�ܪ�����`�`�N��Q�����{�O�P�ʪ��ԭz�B�y�g���X�_�ӡA�Φ��S�����M���ӤS�`�㪺����C�b�m�d�D�������n���A�������@���֤ߧζH�ް_�F�L��_�@�ɪ���ҡA�q�L���p�Q��H�ͤ����������M���æb��`�h���~���A�p�Q��y�I�_���ں믫�����^�����a�O�i����--�{���O�Q�H�B���P�O�z�ʥ�´�b�@�_�A�e�{�X�R���`�㪺�a���O�믫�C���L�A�o���z�ʻ�j���g�@���ҥH����F�P�R��������A�O����z�F�ͩR�^�窺�P�ʪ��ԭz�B�y�g�O�����}���C�m�d�D�������n���y�g����ӡ������������A�O�㦳�嫬���賡���S�⪺�s�裏�P�������A���O�o���S�����賡�����A���ɤF�@�����^���@�̥ͩR�ҬɡA�Φ��@���S�w���賡�a��A�P�ɤ]��ܥX�@���S�w�H�崺�[���賡�a��O�O�S�����۵M���[�����}���G�o���s���ϡ���۵M���[�O�믫�B�_���Ҫ��H���̦Z������A�J�G���S���ɵۨϭ��^�F��@���R�����P���ͩR�ҬɡC��_�P�ܨӻ��A����ɬ���Ӥ������믫���O�o���賡�a�誺�H���A�L�������۵M���@���A�ר�O�۵M�@���H���믫���̦Z�伵�o�@�I�C�L�g��A�b�����O�@�j���B�ͬ���աB�R�����M�I���~�N�A�L�u���@�Ӽֽ�A�ݰ��G�����H�ѥi�H�Q�I�A�e�i�H�Q�T�A���ѥi�H�Q���A���`���ܤ_�Q�X�v�X�ҧa�H���o�ˡA�L�N�q�d�D���������W���F���b���������A�����쪺�o�e�A�i�����Ӥ��a�ߤ_��쪺�s�J�A�j�W��������E���b�s�Y�W���n�峹��. ���M�A�]���ڭ̦b�W�q�ҫ��X���O�v�ɭP�B�o�Z�h�֪��ͩR�ҬɡC�H�O�۵M�B�_�@�����ۿE�o�����A�A�פ_�N���Ӧa���m��@���賡�����W�ɨ�@���㦳���M�N�q���H��ҬɡC
�@�@��ģ�O�����N�ֺq��������D�̪��v�С�12���H�A�ҥH�A�L�O�P�ܤ��P�A�g�`���{���D�O�賡�믫���d�@�ʪ��������@���C�L�{�����L�O�]�賡�^���믫���]�n�A�]�賡�^���a�衦�]�n�A�]�賡�^�����桦�]�n�A���`���u��O�o���g�a����m�A�o���g�a�W���ڪ���ơK�K�ɥN��y�K�K������۷P���������C�O���M�@�^���C�����Y�j�ѡA�S�O���_�B�_��s�����C�����k�k���a�C�O���A�����D�Ψ졥�賡�D�D�����`�O��P���쥦���Y���O�סAı�X�@������B���X�ۥͪ��h��ժ����A�}�B�`ı�o�z�X�Ӥ@�h�βH�ο@�������C--�ڥH���b�o�Ǥ譱���i��M��졨�賡�믫�����H���C��13�L�j�b�ͩ~�_�C���A1957�~�Q���E�k���Z��O�B�_�s��ӳh�a���C�ð��쪺�̤U�h�A�]���L��賡�����d�@�ʪ��ͦs�B�Ҧ��@���`�J���誺�P���C�O�L���P�N�H�ۤ�A��ģ���ȱN�ӤH���d�@���v�@���ϫ���ڡB��a���d�@������A�}�B����O�N���W�ɨ�@���H�����M���d�@�B�Ҫ��a�B�C�����a�N��ģ���o�@���ܦE�w�b1986�~�A�{�����b�o���e�A��ģ�O���۶Dzβ{��D�q�����b�q�L���[�~�H���y�z�A�F��D�[�籡���ت��K�K���{�b�ֺq�����d�@�믫�A�h�O�H�~�w�N�Ѭ����e�A�H���c�B�O�D���Э㪺�Dzδd�@ɲ�ȧP�_�A�i�ܪ��O�Q�y���쪺�W���C���ӱq1986�~�_�A�L�����V����ʧ籡���A���l�D�֪��h�q�ʩM�a�g�ʡ��A����V��t�z�M�H�Ͷ��q�����M���A�L���d�@�N�Ѥ]�o�ͤF�Q�ܡA���L�Q�@���H�����ͦs�J�R�`�`�a�̦��F���A�o�O���@���إߦb�H���ͩR�N�ѤW���s���d�@�N�ѡ��A���@���W�\�Q�B�W�Q�`���H���s�b�������d�@���A�o�@�ɴ��A�����d�����@����ģ�d�@���P���^�{�A�D�n�}�����{�b�^���D�q���d�@�R�B���i���A�Ӫ��{�b�����`�ͦs��ϩҶi�檺�ڤ[���H��ɵ��O�����C��14�p�G�N���z�Ѭ��@���z�Q�ƪ�²ϡ���y�z�A�o�j�^�W�O�@���i�H�������E���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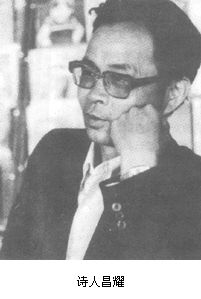
�@�@�m�������~�n15�g�_1988�~���A�ݤ_�Z�@���q���֡A�����²ϡ�ӧ����a���{�F��ģ�����z�F�賡�a�誺�d�@�믫�ҹF�쪺���סC��ģ�ۭz�A�b�o�@���q�A�L���w���Ӳߤ_�q�@�Ө��ץh�{�ѹ�H�A���Ӳߤ_�M�䱩�@�����סA���Ӳߤ_���[���ζH�P�����A�{�����֪��y�q���O�ֻy���h�q�ʩM�h�z�ѩʪ��ͦs�Ŷ����A�m�������~�n�ԭz���h���שʡB�g������H�ʡB�d�@�Nĭ���h�q�ʥ��O�o���ֺq�N�Ѫ����㩺�H�C�ֺq�@�}�l�N�H²ϡ���N�H�ĵe�X�@�T�籡�D�H���t�W�����żv�G�������C�@�h���ߪ����v�C�b�e���C���ۤ@�y�ۯ}���a�����ۡG�����O�ڦP�ɼǦ⪺�����M�Z�@�_�h�J��G�_�ۡH���Ĥ@�y�yø���żv�A��M�O���b���~�ҤİǥX���A�ĤG�y���籡�h�����q�ߨ��o�X�A�u�u��y�w�g�t�t�F���I���ܴ��C�ۡA���I�S�ഫ���o�ӯ��b�e�������ת��籡�D�H���������A�L�����ɦV���B������j���L�����i�G
�@�@�t�W���������~�I�I���m�ڤj
�@�@�Ϥ@���i��F�ʦۻF�l�N�N��Ѧӥ��h�u�ʡC
�@�@�ӥû����p�C
�@�@�t�W�������C
�@�@�L�n�����`�C
�@�@�L�n���Y���C
�@�@�o���b���{��������j�ɧ����O��H���A���L�@�էήe������n�~�A�ȶȧ@�F�@�y�ޥӪ��y�z�A�Ҧ����i��F�ʡA�ۥ@�ɤ���b���������~�m�j���@�}�l�N�`�w�|�Q���Ѧ��k�_�I�I�A�o�O�y�z�A�]�O����--���������J�O�m�����諸�A�o�]�O���H�]��s�j�y�y�ӷ|�f�M�˯��B�[�M�\�U���C�b�H�����N�q�W�A������ۥ@�ɡA�]����۱J�R�A�@�����L�B������ʦb�o���u��O���L�n�����`/ �L�n���Y�����A���ǧ籡�D�H���n�۱��G���t�W��������. �u�u���L�y�֥Ω�H���y�z�w�g�ζH�a��ܥX�@���s�諸�Ѧa�A�@����@�W�ߪ��ҬɡC�ۡA���I���E�b�@�ӿW��_�Ѧa�������Ȧ�̨��W�A�]�P�ɤޥӥX���b���W�����D�D�X�X��ģ�H�^���֪����ޥ����D�b�_�f���a�表�����ۥѴ��g�G�ڼg�ڡ����i�������a���A�G�ӤU�����֥y�������}�F�`�W�A���O�@��֡A���o�O�K�ӳ�y�զ�������L�@��֡A�۵M�A�A�i�H�⥦���}��Ū�A����´�b�@�_����y�o�����A���@���z���L�a�Ӫ���P�Pı�A�O�e�������w�C���`�����������@�����A�Ӵy�z�]�ѫe������H�m�����y�g��Ƭ����J�ӵZ�A�L�G���q�v�����S�g���Y�G
�@�@�@�ӽ��Y�������Ȧ�̦��b�m���������A�@�u�R�¤F���T���˦��b�L���I�n�A�@�ڥR�@������Ҵξ��b�y�ڡC�L���K����_�C�ߤ�����ǥզ��p�`�ܡC�L���V�s�e¼�p���t�m�C�L�C�j�������]���]�����Ӧb�ݮ��C�ڪ�ı�L���ȴ��]�O�ڪ��ȴ��C�ڪ�ı�զ��L�����^���@�����]���O�զ��ڪ����^���@�����C�ϥL�W�e����]�]�O�ϧڦP�˭W�e����]�A�ӧڷP���쪺�w�֫o�����O�L���w�֡C
�@�@�o����Ӫ��yø���ڭ̤İǥX�@�Ӭ��F�l�D���\�Ӹq�L���U�a�e�檺�Ȧ�̧ζH�A�ϤH�_�ʪ����ȬO�L��ͬż�B�h�a�B�h�ΡA��O�L�����@���L�e�a�e�檺�ζH--�ڭ̪�ı�a�P����o�˪��Ȧ�̤@�w���@�ӭȱo�L�l�D���ت��O�@���H�����伵�A�o�L�G�O�@�ӨD�D�̪��ζH�C�ȱo��Ҫ��O�A�o�ӮȦ�̬O�{�ꤤ���A�٬O�ȶȬO�籡�D�H���Q�H�����H�i�ӡA�L�O�L�h���B�{�b���B�٬O�N�Ӫ��H�o�ǰ��D�]�\�}�����n�A�]���L�i�H�O�䤤�����N�@���C�L�Ʀܥi�H�O���ڡ����L�h�B�Ϊ̬O���ڡ����t�~�@�Ӥ���--�M�ӵL�O�֡A�@���L�e�a�b���W�樫���L�A�O�]���g�p���e�檺���ڡ������o���j�F�L�ɪ��Z��--�Y�ϦP�O�l�D�̡A�Y�ϦP�ɷN�Ѩ즳�P�����s�b�A����^�ӻ����M�O�������t�W�A�_�O���y�n�۹����֪��D�D�y�@�˭��s�T�_�G
�@�@�ӷU�q�I�����o�u�O�F��I��/ ���O�ڦP�ɼǦ⪺�����M�Z�@�_�h�J����_�ۡH
�@�@�ֺq�U����V�o�Ӧb���W���Ȧ�̪����I�A�L�����b���~�������A���������ܡC/ �������b�C/ ���������C�����I���W�S���ɨ�@���尪�尪���a��A�]�\�O�q�ѤW���W�Ҫ����סA��ӶS�����N�H�A�N�������۵M�S��������p���F��G�����s�ʭ��p�P�������^��b�����ʪ����[�C/ �h�A�����p�P�A��֡C����Ū��U���@�y�A�ڭ̥i�H�̻{�o�N�O�W�Ҫ����I�G
�@�@�@�ӬD�Ԫ��Ȧ�̨B��b�W�Ҫ��F�L�C
�@�@�S�����N�H�N�W����O�j�������~�����������@�F�L�A�b�W�Ҳ����A�]�\�H�@���l�D�`�w�N�����Ʀb�F�L���樫���˥i���a�H�o�ӷN�H���@���J�R���d�@�ʡC�M�ӶS�����N�H�b�o���o���ͤ@���R�����Pı�A�]���o�����@���O�J�R�ܪ����믫�A�@���ﱵ�W�Ҫ��D�Ԫ��믫--����s�諸��������ҶH�����@�ɡB�R�B�A�H�]�\�O���p���A�M�ӥL���������}���N�ӡA���F�ت��M���}�𪺰l�D���믫�A�o�O�L�k�Q���`���K�K�_�O�ֺq�ޥӥX�@�ӬJ�O�g�ꪺ�S�O�H���������G
�@�@���e��/ �@�s�ȴ�̤���s�~��߱�ѻ����A�H�Z/ �N�Ų~�r�O���Y�b�}�����~�����C/ �@����v�в����C/ �@�a�H���p�P��ҦӥO�k�I�ʮe�C/ �����}�_�C��
�@�@�b�o���A��ߪe�����@�s�ȴ��--���Ӥ]�]�A���өt�W���籡�D�H���O���Ӱ��۪��Ȧ�̧a--�E�b�@�_�A�i��@�������s���`�������C�o�����@���F���o�a�������A�����_���o�̹F���o�a���Z���Y���g�g�X�X�M�ӡA�o�������o���@���d���Ʀܴd�[����m�A�ϱo�S�p���o���������欰���G�S�[�W�F�@���ƨg���Ūn�]���G�B�������֤��`�X�{�����Ǧ�������B����G�_�ۡ��A����ģ�ֺq���g�`�X�{�����P���C���СC��w���B�����������@�ˡA�O�@���d�a�ҬɡC�ȶȳ]�Q���������s�b�e���g���̦Ƕ¦⪺�żv�A�������֤����J���誺�t�W�P�O�J�R���d�@�P�N���M�O���H�����C�F�졧�ت����o���M���@���d�[�P�X�X�o���t�V���F�F�֤H���{�N�P�G�֨������Ȧ�̡����M�O�@�Ӳz�Q�D�q�̡A�M�Ӹg�L�h�֦~���W���A��@�ɪ����եL�S���@���M�����{�N�N�ѡA�e��ۥL���Q�H������Ȫ��A���O�@���j�妡�����I���l�D�A�ӬO�@���L���I�����Ӫ��樫�A�S�p�B�h�w�A�û�����F�����L�Pı�ɵ��ɬ��B�i�H���A�e�檺�ҬɡC�ҥH�ֺq���̦Z��y�t�t�F�@�Ӻ}�媺���������N�H�G�s�~���H���p�P������ҡA�Ӿ�Ӥ����{�p���b�����@�˺}�B�_�ӡK�K�o���O�@�������U�Ӫ��R��A�ӬO���M�R���F�d�[���ͥͤ������ʷP�C
�@�@��ģ���o���֡A�C�@�q���i�H���g���O�賡�S�����u�ꪺ���H�A���P�ɫo�S�a���@�p���H����m�A���^�W�S�e��F�@�ӡ����o�������ܵ���--�u�O�b�o���A�����o�����D�D�w�g�t�ର�a�۲{�N�믫�����b���W�����D�D�C�o���������檺�ت��O���\�H�@���H�������e�����A�㦳�h�q�ʡA���i�H�O�@���麥�}�����z�Q�D�q�믫�����H���A�]�i�H�O���ڤ�ƪ����Y���H���A�]�i�H�O�ͩR�������B�H�����������H���A�ͩR���尪���Ҭɪ��H���K�K�����C�b�o�@�I�W�A����ܥX���^�Nĭ���h�q�ʡA���o���h�q���M���@���۹�í�w�������ڭ̧ⴤ�������^�N���A�l�ާڭ̪��A�O�֤������e�������쪺�ҬɡB�����O�ڦ@�ɼǦ⪺�����M�Z�@�_���J��G�_�ۡ�����ϡ�ӹ������t�W�A��������R�B���D�Ըq�L���U�a�e�檺�d�@�믫�C
�@�@�`���G
�@�@1 �Ѿ\����M�m����s��ǵo�i���������һX�DzΡn�A���J�m����M�ۿﶰ�n�A�s��v�S�j�ǥX����1997�~�A��31-55 ���C
�@�@2 �B�д����_�m�g��Ǵ��X�L������h�A�Y�G������Ǫ��ީʭ�h�M���|�D�q�ʽ�F�������R�{��D�q���Ч@��k�F�~�өM�o�i�����Ǫ����ڭ���F�O���M�o���j�P�������a���M�@�����a��S��F�y�g�A�������g�H���M�A�������v�M�ɥN�R�B�C�Ѩ��B�дšm���O�m�g��ǡn�A�K�������X����1984�~���A��95���C
�@�@3 �Ѿ\�B�дšm�q�m�g�r�ǡn�A�m�m�g�n�A�B�дťD�s�A�H����ǥX����1984�~���C
�@�@4 �ަۨL���R�m�q�����p����r�ǡn�A�m�����p����n�A���w�ؽs�A�@�a�X����1988�~���C
�@�@5 �m���١n�A��o�_�m�_�ʤ�ǡn1980�~10�븹�A���Ч����u�m�L���R�����n��1 ���A�_�ʮv�S�j�ǥX����1998�~���C
�@�@6 �ަۨL���R�m�۳��a���n�A���J�m�L���R�����n��4 ���A�_�ʮv�S�j�ǥX����1998�~���A��281 ���C
�@�@7 �P�W�ѡA��290-291 ���C
�@�@8 �P�W�ѡA��292 ���C
�@�@9 �m�ϳ��n��Z�_�m����n1984�~��1 ���C���Ч����u�m�H�ͱ��p����n�A�|�t�����X����1987�~���C
�@�@10�@�ަ۾H�ͱ��m�q�M�X�e�I���r�g�~��y�n�A���m�p����E�n1982�~��2 ���C
�@�@11�@�m�d�D�������n�A��Z�_�m�ѩ�x�����n1984�~8 �븹�C
�@�@12�@�m�֪�§�١n���J�m�R�B����--��ģ�|�Q�~�֧@��~�n�A�C���H���X����1994�~���A��300 ���C
�@�@13�@�P�W�ѡA��297 ��298 ���C
�@�@14�@�ަۧ��E�y�m���������~--�ש�ģ�ֺq���d�@�믫���n�A���m���N�@�a���סn1991�~��1 ���C
�@�@15�@�m�������~�n�g�_1988�~12��12��A���Ч����u�m�R�B����--��ģ�|�Q�~�֧@��~�n�A�C���H���X����1994�~���C
�@�@------------------
�@�@��ۦt�z��ǥ@��
�e�@��
�^�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