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頁
回目錄
第一節 鄉土小說与市井小說
當80年代的文學創作一步步地恢复和發揚現代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和現實戰斗精神的時候,“五四”新文學的另一個傳統,即以建构現代審美原則為宗旨的“文學的啟蒙”傳統也悄悄地崛起。這一傳統下的文學創作不像“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思潮那樣直接面對人生、反思歷史、与社會上的陰暗面做短兵相接的交鋒;也不像啟蒙主義大旗下的文學,總是發人深省地從芸芸眾生的渾濁生活中尋找封建陰魂的寄生地。這些作家、詩人、散文家的精神气質多少帶著一點儿浪漫性,他們似乎不約而同地對中國本土文化采取了比較溫和、親切的態度,似乎是不想也不屑与現實政治發生針鋒相對的摩擦,他們慢慢地試圖從傳統所圈定的所謂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与責任感中游离開去,在民間的土地上另外尋找一個理想的寄托之地。從表面上看,這种新的審美風格与現實生活中作家們的政治追求和社會實踐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鄉土化”或“市井化”風格的追求來掩飾其与現實關系的妥協,但從文學史的傳統來看,“五四”新文學一直存在著兩种啟蒙的傳統,一种是“啟蒙的文學”,另一种則是“文學的啟蒙”1.前者強調思想藝術的深刻性,并以文學与歷史的現代化進程的同步性作為衡量其深刻的標准;后者則是以文學如何建立現代漢語的審美价值為目標,它常常依托民間風土來表達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不盡同步。追溯其源,新文學史上周作人、廢名、沈從文、老舍、蕭紅等作家的散文、小說,斷斷續續地延續了這一傳統。
“文革”剛剛結束之初,大多數作家都自覺以文學為社會良知的武器,積极投入了維護与宣傳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的社會實踐,以倡導和發揚知識分子現實戰斗精神的傳統為己任;但隨著80年代的文學創作的繁榮發展,作家的創作個性逐漸体現出來,于是,文學的審美精神也愈顯多樣化。就在“傷痕”、“反思”、“人道主義”、“現代化”等新的時代共名對文學發生愈來愈重要的作用的時候,一些作家別開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審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鄉土性”、“文化小說”、“西部精神”等一組新的審美內涵來替代文學創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識形態。這類創作中的代表作有被稱為“鄉土小說”的劉紹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等中篇小說,有被稱為“市井小說”的鄧友梅的《煙壺》、《那五》,馮驥才的《神鞭》、《三寸金蓮》,陸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說等,有以家鄉紀事來揭示民間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說,有以家鄉風情描寫社會改革的林斤瀾的《矮凳橋風情》系列,有擬寓言体的高曉聲的《錢包》、《飛磨》等新筆記小說,還包括了体現西北地區粗獷的邊塞風情的散文和詩歌,等等。在文學史上,僅僅以描寫風土人情為特征的作品是早已有之的,“文革”后涌現出來的陳奐生系列、古華的《芙蓉鎮》等小說,在較充分的現實主義基礎上也同樣出色地描寫了鄉土人情。但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里,風土人情并不是小說故事的環境描寫,而是作為一种藝術的審美精神出現的。民間社會与民間文化是藝術的主要審美對象,反之,人物、環境、故事、情節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當時還作為不可動搖的創作原則(諸如典型環境典型性格等)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動搖。“五四”以來被遮蔽的審美的傳統得以重新發揚光大。
在這一創作思潮中有意識地提倡“鄉土小說”的是劉紹棠,他對鄉土小說有過理論闡釋,都是些大而無當的意思2 ,但他自己的鮮明的創作風格倒是体現出他所要追求的“鄉土小說”的特色。他把自己的語言美學命名為“山里紅風味”3 ,大致上包含了學習和運用民間說書藝術、著力描寫鄉土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前一個特點使他的小說多帶傳奇性,語言是活潑的口語,但時而夾雜了舊時說書藝人慣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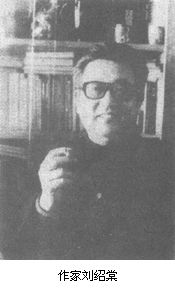 形容詞,民間的气息比較濃厚。他的几部最出色的中篇小說都以描寫抗日爆發前夕的運河邊上農村生活為背景,著重渲染的是農家生活傳奇,俊男俊女恩愛夫妻,一諾千金生死交情,故事結局也總是“抗日加大團圓”。 這樣的故事傳奇自然回避了現實生活中的尖銳矛盾,而且內容結构也常有重复之嫌。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民間語言和藝術因素,可讀性強,在大眾讀物剛剛起步的80年代,在農村會受到歡迎。后一個特點构成了劉紹棠小說的語言特色,其文筆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遠,景物描寫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園牧歌。他歌頌的人情美主要体現在中國民間道德的善良和情義方面,小說中的主人公無不是俠骨柔腸,重情重義,既描畫了民間人情美的极致,也顯示出作家的世俗理想。
形容詞,民間的气息比較濃厚。他的几部最出色的中篇小說都以描寫抗日爆發前夕的運河邊上農村生活為背景,著重渲染的是農家生活傳奇,俊男俊女恩愛夫妻,一諾千金生死交情,故事結局也總是“抗日加大團圓”。 這樣的故事傳奇自然回避了現實生活中的尖銳矛盾,而且內容結构也常有重复之嫌。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民間語言和藝術因素,可讀性強,在大眾讀物剛剛起步的80年代,在農村會受到歡迎。后一個特點构成了劉紹棠小說的語言特色,其文筆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遠,景物描寫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園牧歌。他歌頌的人情美主要体現在中國民間道德的善良和情義方面,小說中的主人公無不是俠骨柔腸,重情重義,既描畫了民間人情美的极致,也顯示出作家的世俗理想。
這一創作思潮中另一個重要流派是“市井小說”,汪曾祺對這個概念有過一些論述,如:“市井小說沒有史詩,所寫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說’里沒有英雄,寫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說的“作者的思想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他們對市民生活的觀察角度是俯視的,因此能看得更為真切,更為深刻。”4 這些論述對有些作家的創作是合适的,尤其是鄧友梅和馮驥才的小說,他們筆下的民俗風情可
 以說都是已經消失的民間社會的重現,既是已經“消失”,就自然有被歷史淘汰的理由,如《那五》所寫八旗破落子弟那五流落市井街頭的种种遭遇,如盜賣古玩、買稿騙名、捧角、票友等等活動,都不是單純的個人性的遭遇,而是作家有意識地寫出了一种文化的沒落。出于現實環境的要求,作家有時在小說里虛构一個“愛國主義”的故事背景,也有意將民間藝人与民間英雄聯系起來,如《煙壺》里,這种舊民間工藝与傳統的做人道德結合為一体,還發出一种類似銅綠鐵銹的异彩。《神鞭》是一部准武俠的小說,對傻二辮子的神乎其神的渲染已經固然游戲成分,而其中傻二的父親對他的臨終忠告以及他隨時代而變革“神鞭”精神的思想,卻体現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精華。由于這些作品描寫民俗是与特定的歷史背景聯系在一起,才會有“俯視”的敘事視角來對民俗本身進行反思。
以說都是已經消失的民間社會的重現,既是已經“消失”,就自然有被歷史淘汰的理由,如《那五》所寫八旗破落子弟那五流落市井街頭的种种遭遇,如盜賣古玩、買稿騙名、捧角、票友等等活動,都不是單純的個人性的遭遇,而是作家有意識地寫出了一种文化的沒落。出于現實環境的要求,作家有時在小說里虛构一個“愛國主義”的故事背景,也有意將民間藝人与民間英雄聯系起來,如《煙壺》里,這种舊民間工藝与傳統的做人道德結合為一体,還發出一种類似銅綠鐵銹的异彩。《神鞭》是一部准武俠的小說,對傻二辮子的神乎其神的渲染已經固然游戲成分,而其中傻二的父親對他的臨終忠告以及他隨時代而變革“神鞭”精神的思想,卻体現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精華。由于這些作品描寫民俗是与特定的歷史背景聯系在一起,才會有“俯視”的敘事視角來對民俗本身進行反思。
也有將民俗風情的描寫与當代生活結合起來的、以民情民俗來反襯當前政策的适時的創作。如陸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在5 0年代就難能可貴地寫出了《小巷深處》這樣有獨創性的小說,文革后他創作了《美食家》、《井》等膾炙人口的中篇小說,尤其是《美食家》,通過一位老“吃客”的經歷反映了當代社會和文化觀念的變遷,歷次政治運動使社會生活日益粗鄙的外部環境与基層當權者內在狹隘的階級報复心理,使有著悠久傳統的江南食文化遭到破坏,但同時真正的民間社會卻在日常生活方式下保存了這种俗文化的精髓。小說敘事者是個對食文化、對老吃客都有著嚴重偏見的“當權者”,由這樣的角色敘述蘇州民俗的美食文化很難說稱職,但通過他的視角來反映食文化的歷史變遷卻有著警世的意義。林斤瀾是浙江溫州人,他的家鄉在改革開放政策的鼓舞下,大力發展個体經濟,迅速改變了貧困落后的局面,但溫州的經濟模式是否符合國家社會主義的預設理想,在學術領域一向是有爭議的,林斤瀾的系列小說《矮凳橋風情》以家鄉人和家鄉事為題材,融現實生活与民間傳說為一体,寫出了別有風味的文化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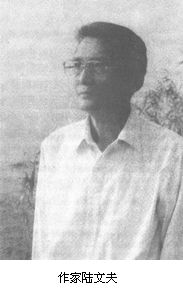
汪曾祺本人的小說創作特點与上述作品不太一樣。如果說,他的創作也采用了他自己所說的“俯視”的視角,那倒不是站在“更高層次”上求得更“深刻”的效果,恰恰相反,汪曾祺的小說不但具有民間風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間立場,其深刻性表現為對民間文化的無間的認同上,并沒有人為地加入知識分子的价值判斷。如果說,在鄧友梅、馮驥才等人的敘事立場上,“深刻”的价值判斷是体現在用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來清理民間的藏污納垢性,而汪曾祺的小說的“深刻”是應該反過來理解,他從真正的下層民間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來衡量統治階級強加于民間的、或者是知識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識的合理性。譬如他在《大淖記事》中他記載窮鄉風俗:
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轎吹鼓手是掙不著他們的錢的。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們在男女關系上是比較隨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個媳婦,在丈夫以外,再“靠”一個,不是稀奇事。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婦相与了一個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錢買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們的錢,反而把錢給他花,叫做“倒貼”. 因此,街里的人說這里“風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風气更好一些呢?難說。
民間的藏污納垢性也表現為封建意識對民間弱者變本加厲的殘害,如小說《白鹿原》所描寫的家規家法,所以汪曾祺才會說“難說”,以表示真正下層民間的多元的道德標准。民間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對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封建傳統道德和知識分子的現代道德下面它是被遮蔽的,無法自由生長,所以才會有文藝作品來鼓勵它、歌頌它和追求它。汪曾祺的可貴之處,就是他站在民間文化的立場上寫出了窮苦人們承受苦難和反抗壓迫時的樂觀、情義和堅強,熱情謳歌了民間自己的道德立場,包括巧云接受強暴的態度、小錫匠對愛情的忠貞不渝以及錫匠抗議大兵的方式,都不帶一點矯情和做派。汪曾祺的小說里所体現出來的民間敘事立場在當時還覺得新鮮,但到90年代以后,卻對青年一代作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創作思潮還融入了來自西部邊疆的民族風土的气息。西部風情進入當代文學,所帶來的不是僅供獵奇的邊緣地區的粗獷景色与風習,而是一种雄渾深厚的美學風貌与蒼涼深廣的悲劇精神。大西北既是貧窮荒寒的,又是廣闊坦蕩,它高迥深遠而又純洁朴素--也許只有面對這种壯麗蒼涼的自然,精神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真正的崇高風貌;只有面對這种生存的极境,人類才能真正体驗到生存的深廣的悲劇精神。西部文學在80年代帶給中國當代文學的,正是這种崇高的美學風貌与深廣的悲劇精神。周濤与昌耀是西部文學中較為重要的作家,他們恰該也分別偏重于表現西部精神這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
------------------
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前一頁
回目錄